点击蓝字 · 关注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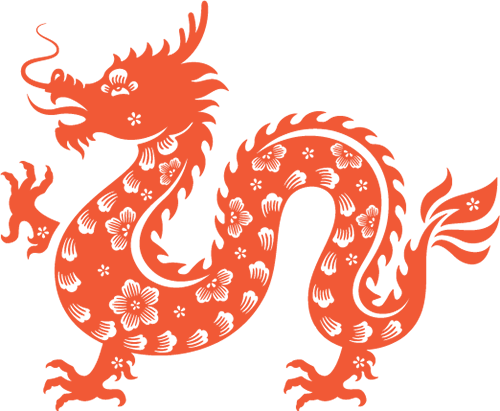
喜迎新春·龙年大吉
过年,又称为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已传承千年之久。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是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在过年这一特殊时刻,人们无论身在何处,都会放下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共度佳节。
在众多文学形式中,散文以其独特的魅力和表现,成为了记录和传递情感、思考和感悟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在描绘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时,散文更是展现出了其独特的韵味和情感深度。让我们来一起欣赏几篇关于春节的散文,感受新春那扑面而来的喜庆氛围!


朱自清●《新年底故事》

昨天家里来了些人到厨房里煮出些肉包子、糖馒头和三大块风糖糕来;他们倒是好人哩!娘和姊姊嫂嫂裹得好粽子;娘只许我吃一个,嫂嫂又给我一个,叫我别告诉娘;我又跟姊姊要,姊姊说我再吃不得了;好笑,伊吃得,我吃不得!后来郭妈妈偷给我一个,拿在手里给我看了,说替我收着,饿了好吃。
肉包子、糖馒头、风糖糕,我都吃了些,又趁娘他们不见,每样拿了几个,将袍子兜了,想藏在床里去;不想间壁一只狗跑来,尽向我身上闻,我又怕又急,只得紧紧抱着袍角儿跑;狗也跟着,我便叫起来。娘在厨房里骂我“又作死了”,又叫姊姊。一会大姊姊来了,将狗打走;夺开我的兜儿一看,说“你拿这些,还吃死了呢!”伊每样留下一个,别的都拿去了;伊收到自己床里去呢!晚间郭妈妈又和我要去一块风糖糕;我只吃了一个肉包子和糖馒头罢了。
今晚上家里桌子、椅子都披上红的、花的衫儿,好看呢!到处点着红的蜡烛;他们磕起头来,我跟着磕了一会儿;爸爸、娘又给他俩磕头,我也磕了。他们问我墙上挂着画的两个人儿是谁?我说“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娘笑说:“这是祖爷爷和祖奶奶哩!”我想他们只有这样大的!呀!桌子摆好了!我先爬上凳子跪得高高地,筷子紧紧捏在手里;他们也都坐拢来。李二拿了好些盘菜放在桌上,又端一碗东西放在盘子中间,热气腾腾地直冒;我赶紧拿着筷子先向了几向,才伸出去;菜还没有夹着,早见娘两只眼正看着我呢,伊鼻子眼里哼了一声,我只得讪讪地将筷子缩回来,放在嘴里咂着。姊姊望着我笑,用指头刮着脸羞我;我别转脸来,骨(鼓)都(嘟)着嘴不睬伊。后来娘他们都动筷子了,他们一筷一筷地夹了许多菜给我;我不管好歹,眼里只顾看着面前的一只碗,嘴里不住地嚼着。嚼到后来,忽然不要嚼了;眼里看着,心里爱着,只是菜不知怎么,都不好吃了。我只得让他们剩在碗里,独自一个攀着桌子爬下来了。
娘房里,哥哥嫂嫂房里,姊姊房里都点着一对通红的大蜡烛;郭妈妈也将我们房里的点了,叫我去看。我要爬到桌上去看,郭妈妈不许,我便跳起来嚷着。伊大声叫道:“太太,你看,宝宝要玩蜡烛哩!”娘在伊房里说:“好儿子,别闹,你娘给好东西你吃!”伊果然拿着一盘茶果进来;又有一个红纸包儿,说是一块钱,给我“压岁”的,娘交给郭妈妈收着,说不许我瞎用。我只顾抓茶果吃,又在小箱子里拿出些我的泥宝宝来:这一个是小娘娘八月节买给我的,这一个是施伟仁送我的,这些是爸爸在上海买来的。我教他们都站在桌上,每人面前,放些茶果,叫他们吃。呀!你们怎么不吃!我看见娘放好几碗菜在画的人儿面前,给他们吃;我的宝宝们为什么不吃呢?呵!只怕我没有磕头罢(吧),赶快磕头罢(吧)!
郭妈妈说话了;伊抱着我说:“明天过年了,多有趣呢!”粽子,包子,都听我吃。衣服,鞋子,帽子都穿新的——要“斯文”些。舅舅家的阿龙、阿虎,娘娘家的毛头、三宝都来和我玩耍。伊说有许多地方耍把戏的,只要我们不闹,便带我们去。我忙答应说:“好妈妈,宝宝是不闹的,你带了他去罢(吧)!”伊点点头,我便放心了。伊又说要买些花炮给我家来放,伊说去年我也放过;好有趣哩!伊一头说,一头拍着我,我两个眼皮儿渐渐地合拢了。
我果然同着阿龙、阿虎他们在附近一个大操场上;我抱在郭妈妈怀里,看着耍猴把戏的。那猴儿一上一下爬着杆儿,我只笑着用手不住地指着叫“咦!咦!”忽然旁边有一个人说,“他看你呢!”我仔细一看,猴儿果然在看我,便吓得要哭;那人忽然笑了一个可怕的笑,说:“看着我罢(吧)!”我又安了心。忽然一声锣响,我回头一看,我已在一个不识的人的怀里了!我哭着,叫着,挣着;耳边忽然郭妈妈说,“宝宝怎么了,妈妈在这里。不怕的!”我才晓得还在郭妈妈怀里;只不知怎么便回来了?
太阳在地板上了,郭妈妈起来。我也揉着眼睛;开眼一看,桌上我的宝宝们都睡着了——他们也要睡觉呢。青梅呢?我的小青梅呢?宝宝顶顶喜欢的青梅呢?怎么没了?我哭了。郭妈妈忙跑来问什么事,我哭着全告诉了伊。伊在桌上找了一阵;在地板上太阳里找着一片核子,说被“绿尾巴”吃了。我忙说,“唔!宝宝怕!”将头躲在伊怀里;伊说,“不怕,日里他不来的,你只要不哭好了!”我耍起来,伊叫我等着,拿衣服给我穿;伊拿了一件花棉袄,棉裤,一件红而亮的袍子,一件有毛的背心,是黑的,还有双花鞋,一个有许多金宝宝的风帽;伊帮我穿了衣和鞋,手里拿着风帽,说洗了脸才许戴呢。我真喜欢那个帽,赶忙地央着郭妈妈拿水来给我洗了脸,拍了粉,又用筷子给点胭脂在我眉毛里和鼻子上,又给我戴了风帽;说今天会有人要我做小女婿呢。我欢天喜地跑到厨房里,赶着人叫“恭喜”——这是郭妈妈教我的。一会郭妈妈端了一碗白圆子和一个粽子给我吃了;叫我跟着伊到菩萨前,点起香烛磕头,又给爸爸娘他们磕头。郭妈妈说有事去,叫我好好玩,不要弄污了衣服,毛头、三宝就要来了。
好多时,毛头、三宝和小娘娘都来了。我和他们忙着做菜给我的泥宝宝吃;正拿着些点心果子,切呀剥的,郭妈妈走来,说带我们上街去。我们立刻丢下那些跟着他走。街上门都关着;我们常买落花生的小店也关了。一处处有“斯奉斯奉昌……镗镗镗镗鞈”底(的)声音。我问郭妈妈,伊说是打锣鼓呢。又看见一家门口一个人一只手拿着一挂红红白白的东西,一搭一搭的,那只手拿着一根“煤头”要烧。郭妈妈忙说:“放爆竹了。”叫我们站住,用手闭了耳朵,伊说“不要怕,有我呢。”我见那爆竹一个个地跳了开去,仿佛有些响,右手这一松,只听见“劈(噼)!拍(啪)!”,我一只耳朵几乎震聋了,赶紧地将他(它)闭好,将身子紧紧挨着郭妈妈,一动也不敢动。爆竹只怕不放了,郭妈妈叫我们放下手,我只是指着不肯放;郭妈妈气着说:“你看这孩子……”伊将我的手硬拖下来了。走了不远,有一个摊儿;我们近前一看,花花绿绿的,好东西多着呢!我央着郭妈妈买。伊给我买了一副黑眼镜、一个鬼脸、一个胡须、一把木刀,又给毛头买了一个胡须,给三宝买了一个胡须。我戴了眼镜,叫郭妈妈给我安了胡须;又趁三宝看着我,将伊手里的胡须夺了就跑,三宝哭了,毛头走来追我。我一个不留意,将右脚踏在水潭里,心里着急,想娘又要骂了。毛头已将胡须拿给三宝;他们和郭妈妈走来。伊说我一顿,我只有哭了;伊又抱起我说:“好宝宝,别哭,郭妈妈回来给你换一双,包不叫娘晓得;只下次再不许这样了。”我答应我们就回来了。
今晚是初五了。郭妈妈和我说,明天新衣服要脱下来,椅子桌子红的,花的衫儿也不许穿了,粽子、肉包子、糖馒头、风糖糕,只有明天一早好吃了;阿龙,阿虎他们都不来了;叫我安稳些,好等后天上学堂念书罢(吧)!他们真动手将桌子、椅子底衫儿脱下,墙上画的人儿也卷起了。我一毫不想玩耍,只睡在床上哭着。郭妈妈拿了一支快点完的红蜡烛,到床边问道:“你又什么了?谁给气宝宝受;妈妈是不依的!”我说:“现在年不过了!”伊说:“痴孩子,为这个么?我是骗骗你的;明天我们正要到舅舅家过年去呢!起来罢(吧),别哭了。”我听了伊的话,笑着坐起来,问道:“妈妈,是真的么?别哄你宝宝哩。”
(注:文章标题及文中的“底”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目前写作“的”
向下滑动查看所有内容


老舍●《过年》

最怀念的,还是小时候过的年。
早起拉开窗帘举目望去,一夜之间,外面已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今年冬天雪下得少,似乎缺了一点气氛。这场雪的到来,提示着人们,年已经不远了。是啊,又要过年了,甚至能看到被大雪压弯的树枝也在抖动着春的喜悦。
过年,在感觉中已经有些遥远,甚至没有太多的期盼。在繁忙的都市里,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年味越来越淡,有的时候马上过年了,才想起来。最令自己怀念的,还是小时候过的年,虽然那是些久远的回忆,但一切又都是那样鲜活。
我的老家在农村。一到腊月,年的气氛就浓起来了。在村里的供销社,购年货的人络绎不绝。那些传统的年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想起来是依然漂亮,那厚厚的纸,散发着油墨的芳香,在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把它当作是年的象征。
北方的腊八,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它的特殊意义在于向年又近了一步。每天天没亮就会醒来,一想到要过年了,兴奋的睡不着。
村里的老人们开始对小孩子们说:“小孩小孩你别谗,过了腊八就过年。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孩子们嘻笑着、欢呼着,跑走了。那个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家都能杀得起年猪。而杀了猪的人家都要安排一顿饭,招待一下村邻亲威。我们这些小孩子吃不多少肉,就是图个热闹,屋里屋处的乱窜。
那个年月伙食很差,平时就是苞米面饼子、小米饭,连面食也吃不到。所以过年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那是个解馋的好机会。除夕的前几天,母亲便开始忙着蒸年糕、蒸馒头,前一天才会用大锅烀肉。我则在站在锅台边,紧紧地盯着锅,闻着那飘出的香气,不知不觉着唾液已经流了下来。母亲在旁边看了,便会掀开锅盖,用筷子扎出一小块肉放在碗里,我伸手就拿,顾不上烫嘴,狠狠地咬下去。
我喜欢啃冻梨,吃时发出的“沙沙”声,那白白的梨肉带来的酸甜,总让我回味不尽。当然,也只有过年时才能买梨吃。
有一件小事很是难忘:那次母亲买来了冻梨,放在了储存杂物的仓子里。我便偷偷地盯着她,直到她进了屋子。我一溜小跑来到门前,小心翼翼地打开仓门,钻了进去,把关好门,掏了一个梨子就啃。不一会儿母亲进来取东西,一下子看到了我,我竟然有些不好意思,她却笑了笑,拍了拍我的头,没有说什么。吃晚饭的时候,弟弟还在问母亲:“梨什么时候买啊?”我在心里说:哈,我已经先尝到了。
对联也是过年不可缺少的重要物品。那时候的对联和现在不同,都是买来大红纸请人手写的。父亲的书法很好,是我们村里知名的先生,所以到我家来求父亲写对联的人都排成了队,过年的这两天是父亲最忙碌的时候。我在旁边地看着那黑亮亮的毛笔字写在红纸上,有说不出的羡慕。当红红的对联贴到墙上门上,那个喜庆啊,年的气氛立刻就出来了。
小时候的我喜欢穿新衣服。除夕的头天晚上我会把新衣服拿出来,翻过来掉过去地看,想象着明天就要穿上了,那个高兴啊。一年到头能穿新衣服的时候是很少的,一般都要到过年。睡前早早地把小脚洗干净,把新鞋、新袜摆在枕边看着,后来就睡着了。有时会做梦,虽然不知道自己当时的表情,但小脸上肯定带着甜甜笑意。
除夕也叫年三十,家家张灯结彩,人人喜气洋洋。在那个年月,恐怕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看到大伙的脸上洋溢的笑容。除夕一大早,我就被鞭炮声从睡梦中惊醒。父亲也会在我们的耳边说,快起床吧,过年了,早点放鞭炮。我们便一咕噜地爬起来,穿好新衣服、新鞋,跑到外面放鞭炮。然后等待我们的便是饭桌上香喷喷的饺子了。
我们北方过年的高潮是除夕之夜,最重要的活动叫发纸,一般都是在子时,也就是二十三点到凌晨一点。传说那时候南天门会打开,天上的神仙会鱼贯地下到人间,所以各家有供奉神灵的,都要出去“请”。当然,也有的人说,相当有“福气”的人会看到南天门开,那样的人以后一定会享受荣华富贵,只是没有人能证实罢了。
在欢笑声中白天很快就过去了。夜色渐浓,万家灯火在冬夜里跳动着,映衬着白白的雪,描绘成乡村最美丽的夜晚。除夕的夜充满了祥和与神秘。在人们的眼里,从这里仿佛能看到美好的明天。
在发纸前父亲总是提前把鞭炮拴在一根大杆子上,靠在墙角就等着放了。十点左右,周围的村子就开始发纸了。鞭炮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火光将天边都映得发亮。十一点半了,父亲便把我们几个都叫出去,开始忙活,有的点鞭炮,有的点一堆火,母亲则在屋里做饭。篝光燃起,鞭炮声也响彻夜空。火光映着红红的笑脸,我们围着火堆跳着,叫着,跑着,那一刻,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三十的晚上是要吃年夜饭的。全家人坐在一起,团团圆圆地吃着饭,说说话,其乐融融。这时吃的饺子都是肉馅的,还会在里面放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的话那就预示着一年将有好运相伴。小时候,一次哥哥给我夹了一个饺子,我便边吃边玩,大伙也吃的热火朝天,可是盘子都见底了也没吃到硬币,最后在我的小屁股下面发现了它。
年夜饭后有“守岁”之说,所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据说要是能一夜不睡的话,一年之中头脑都清醒。我们几个小伙伴打着灯笼,出去玩,到别人家的院子里拣落在地上的鞭炮,有的回来之后还可以放。当然,如果玩累了,随便到哪家,都会好吃好喝地招待我们。
难忘的年夜总是过得很快。天亮了,村边响起了欢快的锣鼓声,原来是大秧歌开始拜年了。人们相互拜年,串门,整个小村又在年的气氛中沸腾起来。
时隔多年,一些往事都已淡忘,但儿时过年的情景却永远地留在了心中。
向下滑动查看所有内容


鲁迅●《过年》

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
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谓之“废历”,轻之也;或者谓之“古历”,爱之也。但对于这“历”的待遇是一样的: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
虽过年而不停刊的报章上,也已经有了感慨;但是,感慨而已,到底胜不过事实。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经叫人终年奋发,悲愤,纪念。但是,叫而已矣,到底也胜不过事实。中国的可哀的纪念太多了,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可喜的纪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动分子乘机捣乱”,所以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的庆贺——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向下滑动查看所有内容


梁实秋●《北平年景》

过年须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而所谓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上无双亲,下无儿女,只剩下伉俪一对,大眼瞪小眼,相敬如宾,还能制造什么过年的气氛?北平远在天边,徒萦梦想,童时过年风景,尚可回忆一二。
祭灶过后,年关在你迩。家家忙着把锡香炉,锡蜡签,锡果盘,锡茶托,从蛛网尘封的箱子里取出来,作一年一度的大擦洗。宫灯,纱灯,牛角灯,一齐出笼。年货也是要及早备办的,这包括厨房里用的干货,拜神祭祖用的苹果干果等等,屋里供养的牡丹水仙,孩子们吃的粗细杂拌儿。蜜供是早就在白云观订制好了的,到时候用纸糊的大筐篓一碗一碗的装着送上门来。家中大小,出出进进,如中风魔。主妇当然更有额外负担,要给大家制备新衣新鞋新袜,尽管是布鞋布袜布大衫,总要上下一新。
祭祖先是过年的高潮之一。祖先的影像悬挂在厅堂之上,都是七老八十的,有的撇嘴微笑,有的金刚怒目,在香烟缭绕之中,享用蒸* ;,这时节孝了贤孙叩头如捣蒜,其实亦不知所为何来,慎终追远的意思不能说没有,不过大家忙的是上供,拈香,点烛,磕头,紧接着是撤供,围着吃年夜饭,来不及慎终追远。
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年菜是标准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连下水带猪头,分别处理下咽。一锅纯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末墩儿,鱼冻儿,内皮辣酱,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管够,初一不动刀,初五以前不开市,年菜非囤集不可,结果是年菜等于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后已。
“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这是乡下人说的话,北平人称饺子为“煮饽饽”。城里人也把煮饽饽当做好东西,除了除夕宵夜不可少的一顿之外,从初一至少到初三,顿顿煮饽饽,直把人吃得头昏脑涨。这种疲劳填充的方法颇有道理,可以使你长期的不敢再对煮饽饽妄动食指,直等到你淡忘之后明年再说。除夕宵夜的那一顿,还有考究,其中一只要放进一块银币,谁吃到那一只主交好运。家里有老祖母的,年年是她老人家幸运的一口咬到。谁都知道其中作了手脚,谁都心里有数。
孩子们须要循规蹈矩,否则便成了野孩子,唯有到了过年时节可以沐恩解禁,任意的作孩子状。除夕之夜,院里洒满了芝麻秸儿,孩子们践踏得咯吱咯吱响,是为“踩岁”。闹得精疲力竭,睡前给大人请安,是为“辞岁”。大人摸出点什么作为赏赍,是为“压岁”。
新正是一年复始,不准说丧气话,见面要道一声“新禧”。房梁上有“对我生财”的横披,柱子上有“一入新春万事如意”的直条,天棚上有“紫气东来”的斗方,大门上有“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的对联。墙上本来不大干净的,还可以贴上几张年画,什么“招财进宝”,“肥猪拱门”,都可以收补壁之效。自己心中想要获得的,写出来画出来贴在墙上,俯仰之间仿佛如意算盘业已实现了!
好好的人家没有赌博的。打麻将应该到八大胡同去,在那里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还有佳丽环列。但是过年则几乎家家开赌,推牌九、状元红、呼么喝六,老少咸宜。赌禁的开放可以延长到元宵,这是唯一的家庭娱乐。孩子们玩花炮是没有腻的。九隆斋的大花盒,七层的九层的,花样翻新,直把孩子看得瞪眼咋舌。冲天炮、二踢脚、太平花、飞天七响、炮打襄阳,还有我们自以为值得骄傲的可与火箭媲美的“旗火”,从除夕到天亮彻夜不绝。
街上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里面常是锣鼓齐鸣,狂擂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一年的怨气。大姑娘小媳妇擦脂抹粉的全出动了,三河县的老妈儿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出动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于是厂甸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看,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土地祠里的书摊画棚,看热闹的多,买东西的少。赶着天晴雪霁,满街泥泞,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人们在冰雪中打滚,甘之如饴。“喝豆汁儿,就咸菜儿,琉璃喇叭大沙雁儿”,对于大家还是有足够的诱惑。此外如财神庙、白云观、雍和宫,都是人挤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冻得通红。
新年狂欢拖到十五。但是我记得有一年提前结束了几天,那便是“民国元年”,阴历的正月十二日,在普天同庆声中,袁世凯嗾使北军第三镇曹锟驻禄米仓部队哗变掠劫平津商民两天。这开国后第一个惊人的年景使我到如今不能忘怀。
向下滑动查看所有内容


莫言●《故乡过年》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向下滑动查看所有内容

最是书香能致远,
“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唤醒阅读意识,推广阅读理念,培养阅读习惯,引导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喜欢读书、爱上阅读。期待孩子们成为一颗颗阅读的“种子”,将热爱阅读的基因播撒到身边的每一个角落!
共享阅读·书香翔安

相关文章

【2024年 第18期·桃源故事】《过年的传说》
龍 读书是一件美好而快乐的事, 生活除了诗和远方还有认真看绘本, 小小的我们去揭秘绘本故事里的 奇妙事迹发现新的小乐趣。 壹 故事简介 大怪兽“年”,每到除夕这天,就会来到人类居住的地方,吞食生命。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跑到深山老林里藏起来,躲避“年”的追杀。 有一年除夕,村外来了个乞讨的老人。他身穿大红袍,用大红纸、红蜡烛、鞭炮赶跑了大怪兽“年”。 从此,每年除夕,家家户户都会在门上贴红对联,在门口 […]

世界湿地日,戳这里!
世界湿地日 World Wetlands Day 世界湿地日 每年的2月2日是世界湿地日。这是湿地国际联盟组织(wiun)于1996年3月确定的。2023年的主题是“湿地恢复”(Wetland Restoration)。 World Wetlands Day is celebrated on 2 February every year. This was e […]

世界防治麻风病日:让我们了解它,战胜它!
科/学/防/治 远/离/疾/病 世界防治麻风病日 帮助麻风病人克服困难 让我们一起做健康的守护者吧 每年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是国际麻风日,又称“世界防治麻风病日”。 今天,温泉镇卫生院跟大家科普的是关于麻风病的十大问题。 麻风病是一种什么病? 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接触传染性皮肤病。主要侵犯皮肤和浅表神经。临床上常有皮肤和神经症状。晚期病人可有眼、鼻、咽喉、淋巴结及内脏损害。 麻风病会遗 […]

【星光讲坛】书香陪伴,“悦”读美好
书香陪伴, “悦”读美好 富兰克林说:“读书使人充实, 思考使人深邃,交谈使人清醒。” 书,是一叶扁舟, 承载着人类的精神财富, 驶向时光的彼岸; 书,是一位挚友, 与你进行思想的攀谈。 从《诗经》《论语》 到《城南旧事》《骆驼祥子》; 从《荷马史诗》《双城记》 到《百万英镑》《柳林风声》…… 无论古今,无论中西, 好书总与我们相 […]

看完满是年味儿的春节品牌海报,归心似箭!
编者按 春节营销,向来走心是最关键的。为大家搜集整理了一波往年的春节除夕走心文案海报参考~ | 艺术留学 | 论文发表 | 收藏鉴定 | 印刷出版 | 收藏合作 VX:ddms888 滴滴出行 必须和同学聚会,必须喝醉,回家是一种信仰! 吃了整整一年外卖,回家的路上睡着了,梦里全是妈妈烧的菜,回家是一种信仰! 风是甜的,雪是暖的 […]

新年创意-营销案例盘点。
新年营销案例盘点 品牌们的新年营销都不约而同地 聚焦在“关系与链接”这一主题; 或是现代与传统的链接, 或是新年与艺术的联合, 广告思维回归生活里的温情, 用创意为即将到来的龙年献上序曲。 2024年1月31日 星期三 内容概览 Preview 01 鄂尔多斯 「花间游龙」新年限定系列服饰 02 古井贡酒 万事不如过年好,龙年更妙 […]
 微信精选 | 微信素材库
微信精选 | 微信素材库


